王小川:大模型創業公司,都要走出互聯網大廠的射程 | DBA同學說
發布時間:2024-09-25 16:51
近日,百川智能與北京兒童醫院簽署戰略合作協議,雙方計劃共同推出“一大四小”五款AI醫療產品,旨在用AI賦能優質兒科醫療資源擴容下沉,以及區域均衡布局。長江DBA首二班同學、百川智能創始人兼CEO王小川這樣解讀這次合作的意義:“我們認為有機會在3年內打造出具有三甲醫院主治醫師水平的AI兒科醫生,相當于造出了100萬個主治醫師,足以覆蓋全國鄉一級的診所。”
百川智能雖為2023年4月首批成立的國內AI大模型公司之一,但在競爭白熱化的C端應用市場中卻鮮少亮相。盡管在此之前,百川智能已推出了“百小應”產品,可與Kimi、豆包等同類產品相抗衡。王小川認為,這是危險的,一旦互聯網大廠集中資源和精力競爭,勝算不大。“走出大廠的射程,是AI創業公司都面臨的問題。
作者 | 趙東山
編輯 | 姚赟
來源 | 中國企業家雜志

王小川
長江DBA首二班同學
百川智能創始人兼CEO
“用大模型造醫生”,是王小川當下正專注做的事。2024年8月28日,百川智能與北京兒童醫院簽署戰略合作協議,雙方計劃共同推出“一大四小”五款AI醫療產品,用AI賦能優質兒科醫療資源擴容下沉,以及區域均衡布局。
王小川這樣解讀這次合作的意義:“我們認為有機會在3年內打造出具有三甲醫院主治醫師水平的AI兒科醫生,相當于造出了100萬個主治醫師,足以覆蓋全國鄉一級的診所。”
大模型廠商們拼搶激烈的C端應用市場中,并沒有看到王小川和百川智能的身影。即便在此之前,百川智能也推出了“百小應”,可與Kimi、豆包等產品競爭。他認為這是危險的,一旦互聯網大廠集中資源和精力競爭,勝算不大。“走出大廠的射程,是AI創業公司都面臨的問題。”王小川說。
歷經一年半的探索,當大模型技術的演進曲線從陡峭趨于平緩,AI大模型廠商們開始變得更務實,一邊探索大模型性能的邊界,一邊關注商業化應用的落地。
但在王小川看來,太多人都是把大模型當成效率工具、計算器、電腦,新的時代到了,人們始終還是在老范式里面想問題。他認為,大模型落地應該是尋找那些知識密度最大且供給不足的行業,找到短缺提高供給,而不是大家一起琢磨出新的一個沒有滿足的需求。
王小川還強調,他不是在用大模型做醫療,是因為醫療才來做大模型的。他發現,大家太容易對技術仰望,但卻對技術產生的成果又是一種鄙視的狀態,覺得有所謂的“奴仆”給我服務,太分裂了。
王小川知道AI大模型造醫生現在還面臨一系列的問題:比如醫療事關生死,技術上到底靠不靠譜?國家政策法律批不批?商業模式怎么建?被問多了后,王小川找到一個特別簡單的答案:“那你怎么看無人駕駛,如果出了車禍,無人駕駛同樣事關生死,能不能上路也有交通法規,這些擔憂不都有嗎?那無人駕駛大家干嗎做呢。”
2個月前,百川智能完成A輪融資,總融資金額達50億元人民幣。目前,阿里、騰訊、小米等科技巨頭及多家頂級投資機構都是其股東。
作為2023年4月成立的第一批國內AI大模型公司,百川智能掌舵人王小川當下的心態如何?他在大模型應用落地方面有哪些思考?如何看待創業公司與互聯網大廠的競爭?帶著這些疑問,我們與王小川進行的對話中,也找到了部分答案。

王小川同學在DBA課堂上
以下為核心要點:
1.大家去年焦慮買不到卡,今年焦慮有卡不知道該干嗎。
2.我是因為醫療來做大模型的,不是用大模型做醫療。在我的世界觀里面,這一代(技術)最大的進展是語言變成了數學,不是多模態的事。
3.太多人都是把大模型當成效率工具、計算器、電腦,大模型公司、投資人、應用方都是這種思路。新的時代到了,我們始終還是在老范式里面想問題。
4.應用落地有兩類現象,我們叫盲人摸象和小馬過河。沒看清世界是盲人摸象,這些人不知道模型為何物,到底是工具還是伙伴;小馬過河是指不清楚自己的定位,不知道自己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。
5.大家太容易對技術仰望,但對技術產生的成果又是一種鄙視的狀態,覺得有所謂的“奴仆”給我服務,太分裂了。
6.走出大廠的射程,是這幾個(創業)公司都面臨的問題。所以大模型創業得走出共識,否則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。如果一個公司被看得特別明白,那就不是一個創業公司了。
以下為對王小川的專訪內容實錄(有刪減):

談入局:大模型造醫生,我早就想好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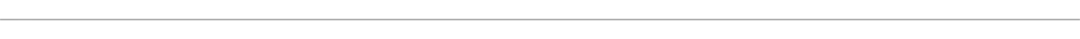
Q:今年落地方面的感受和體驗是怎么樣的?
王小川:去年4月下場時,我提到“超級模型+超級應用”。如何理解模型和應用兩個關系,還有大廠跟創業公司的關系這些問題,那會都已經想明白了。一路走過來,我在技術領域的言論現在已經開始成為共識,比如談到語言比多模態更和智能有關,OpenAI已經開始實踐了,弱化多模態的方向,強化學習要加強。
在應用驅動側,我認為醫療是這波變革中最大的,甚至是唯一的應用。大家找了半天找不著,但是我找著了大家也不信,這是我們自己內部的狀態和在行業中的位置。
Q:一出手就專注在醫療嗎?
王小川:對,去年沒有大聲喊。我是因為醫療來做大模型的,不是用大模型做醫療。其實,在我的世界觀里面,這一代(技術)最大的進展是語言變成了數學,不是多模態的事。
語言變數學,是人類文明中的重大進步。上一次是把物理變成了數學,是牛頓干的,寫了《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》,于是這就變成一個數學問題,這是了不起的進步。這一次,語言背后的知識、思考、溝通就變成數學問題了。語言變數學之后就知識、思考、溝通變數學,這是最大的變化。
因此,我認為未來的東西是做生命的數學模型。造醫生不是一個垂直語言問題,是用AGI走通,用生命模型走的。在我心中,這不是做個垂直的事情,也許應用領域是垂直的,但是用的模型技術是通向未來的。這是我底層的思考,并不是大家講做醫療就是做垂直應用去了。
當然現在醫療還面臨很多質疑:技術上到底靠不靠譜?事關生死那是非常嚴肅的,國家政策法律批不批?商業模式怎么建?一堆問題。我后來找到一個特別簡單的回答方法,你怎么看無人駕駛?如果以上問題是不做的原因,那無人駕駛大家干嗎做呢?

王小川同學在DBA活動中
Q:也許大家天然認為醫療場景比駕駛場景要解決的問題更復雜。
王小川:(造)醫生確實比這難,但當你談生命問題和行車法規問題時都是在一個大類里的。醫療是唯一一個要做服務和科研的行業,是因為整個醫學的認知是不足的,必須要在實踐當中找認知,所以不要認為單個醫生多強——滿打滿算,單個醫生一輩子看3萬個病人,但大模型今天能夠把所有的數據放一塊,甚至能像醫生一樣地看1000萬個病人。

談路徑:得醫生者得天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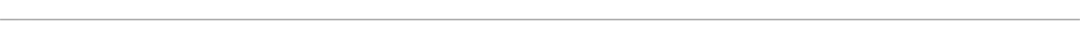
Q:大模型在醫療場景當中,跟醫生的結合,或者對醫生的賦能是什么?
王小川:短期是把成熟醫生的經驗賦能給它,長期會超過醫生。今天我們對技術還處于一種蔑視的位置,之前很多創業者探索過這個領域,更多是模式導向的,連接醫生,但醫生供給不足的問題沒有解決。
2016年我學會了一句話,叫“得醫生者得天下”。互聯網是一個匹配邏輯,拿到一邊去撬動另一邊,或者發現隱藏需求的產品思維模式,成天琢磨的是還有什么潛在的沒有被滿足的需求。但是醫療不是這樣的,醫療是個供給驅動的,你的需求很明白,就是要治病。醫生供給是不足的。
Q:現在您做的事醫院是買單方嗎?
王小川:短期可能是醫院買單,但最終的買單方應該是保險、政府或者個人。在我的邏輯里,不是幫助醫生,是造醫生,我們不是在院內,是要走向院外。醫生對我們而言是朋友關系,但不是我們的服務對象,他是我們的合作伙伴。
我們已經跟北京兒童醫院合作,倪鑫院長明確提出,造100萬個可“居家”的兒科醫生。我們提了一個很大的概念是改變大家的就診路徑:原來技術都是在醫生背后,給醫生提供CDSS,在醫院里做智能影像的讀片系統,而我們是從院內走向院外,甚至從線下走到線上。造醫生這事是必須干的。
Q:為什么是兒科?
王小川:兒科對改變路徑的需求最為迫切。小朋友隔三差五就生病,家長不放心就請假去醫院,甚至半夜要去急診,去了還可能交叉感染,特別是流感大暴發時期。其實80%的兒科疾病是不需要去醫院的,這是院長講的。去醫院就診對患者的成本很高,醫院的體驗也不好,那怎么能讓他別來?就類似國家提倡的分級醫療,通過該路徑實現醫療供給的普及化。
Q:剛剛您反復提到“造醫生”這個詞,相當于它要具備醫生的判斷能力?
王小川:溝通能力、判斷能力。尤其是溝通能力,不是說材料準備好了你幫我做判斷那一下,問診反而是它最核心的能力。問診今天還是刀耕火種,還在靠醫生這張嘴,沒有被標準化過,問題問得不對,就得不到好答案。我們對標的是美國的全科醫生,他會的事兒,我們就該會,他不會的事你別指望我會。
Q:對你來說是一個逐漸打磨的過程,還是第一天起步你就想好要怎樣去做?
王小川:我在2018年說了兩件事:一是“當機器掌握語言,強人工智能就到了”,二是讓數字家庭醫生去賦能基層,這里講的不是在院內的賦能。后來,我還發文章說在未來5到10年可以看到這件事情做起來,就是到2028年。

談思維:不要在過去的范式里思考問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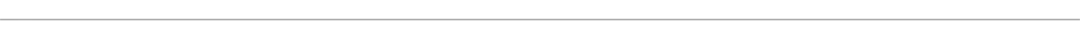
Q:我們一圈聊下來發現很多通用模型公司在找場景落地體驗,大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,醫院這個場景怎么樣?
王小川:太多的行業人都是把大模型當成效率工具,計算器、電腦在想這個事了,大模型公司、投資人、應用方都是這種思路。新的時代到了,我們始終還是在老范式里面想問題。
舉個典型的例子,當時一個頭部公司核心項目的參與人跑來問我,大模型這個事靠譜嗎?我說你為什么問這個問題?他說7位數乘法都不會做。我接著問,那你會嗎?你坐我面前作為高管也不會7位數乘法,為什么要指望它會?
大家的思維出問題了,我們在“造人”,不是在造工具。
實際上,我提的“造人”是造伙伴的角度,大家開始提的概念叫助理。助理就是錯誤的理解,我們老覺得人高級它低級,它是幫你打雜的,我動腦子你動手,助理是幫你動手的角色。有調侃說,我們想讓機器去掃地洗碗,讓人去寫詩畫畫,結果今天機器寫詩畫畫了,人還在掃地洗碗。
今天我們認為更高級的不是在造助理,是造顧問,它比你更有知識。什么行業是知識密度最大且供給不足的?這是正確的打開路徑。找到短缺就要提高供給,而不是大家琢磨出新的一個沒有滿足的需求。
Q:把它當成一個生產力工具的想法從根上就有錯?
王小川:對。大家老說(要做的)要么殺時間的,要么省時間的。殺時間是娛樂化的,省時間是提效的。那老師、醫生、律師是殺時間的,還是省時間的?都不是,不要在過去的范式里思考問題。
Q:跳出百川智能來看,大家在商業化的路徑走過或正在走哪些彎路?
王小川:一種是,我認為是“有眼下沒未來”,比如立刻就賺到快錢的,你寫個廣告文案、寫個PPT效果很好,沒問題。但這只是一個小應用,在技術迭代過程中,不會成為主旋律。
另一種,覺得訓練模型之后場景自然會來。這個我也不太認可,還要思考大模型跟搜索是什么關系,跟強化學習什么關系,都要完整思考,不是在一個單點上發篇論文就叫技術。
Q:希望應用模型的企業,你看到他們對模型都有哪些誤區?
王小川:大家有點好高騖遠,原來很多垂直產業互聯網立馬想的就是我要訓練模型,轉身從需求方變成了供給方。好多人找我們,問能不能幫我訓個模型?我問他需求啥?他說我也不知道需求啥,反正我訓個模型給別人用。
應用落地有兩類現象,我們叫盲人摸象和小馬過河。沒看清世界是盲人摸象,這些人不知道模型為何物,到底是工具還是伙伴;小馬過河是指不清楚自己的定位,不知道自己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。

談能力:對醫療有更多的理解和信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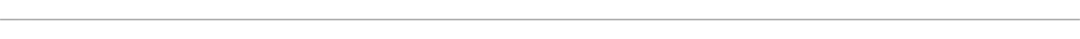
Q:做醫療垂直大模型中間能力的匹配或者需要的切換是?
王小川:我從沒把它當成垂直模型,我們叫醫療增強。通用模型解決不了醫療問題,對我來講,核心是需要讓團隊對醫療有更多的理解和信仰。信仰和理解,這是需要事件和過程的。前段時間我正好跟我們的技術同學講,如果半年前讓你往醫療上想你啥想法?他說我可能離職不干了,但現在呢?覺得真好。
我們跟北京兒童醫院合作的核心是用他們的數據造“醫生”,造醫療大模型,讓“醫生”跟患者、家長能直接接觸到。
Q:這樣的話,對團隊的能力要求很高,他們既要是AI專家,又要懂醫療。
王小川:我們有醫生團隊,甚至有醫生還會寫代碼。醫療圈的人,之前最大的特點就是做“傷”了,講什么都不興奮。但是,當和他們講到大模型造醫生時,有少量的人能興奮,甚至他們還想參與、貢獻,那就是特別優秀的人選。
Q:之前醫院的數據是數據孤島,這種情況下,作為模型公司涉及這個問題嗎?
王小川:我覺得有問題,但我知道醫療是比其他行業更有數據的地方了。這個行業已經有一定的數據沉淀,數字化也做得不錯了,很多行業數字化都沒有。
Q:現在大家有個說法,大模型推理速度會降下來。
王小川:對,一頭是會數十倍地往下降,但是另一頭也會是十倍甚至千倍地往上漲。因為讓機器開始學會慢思考了,它推理完之后不是給你一個靈光一現的東西,它需要慢思考。這時,對推理的要求會變高。比如說,OpenAI會變慢,至少要思考10到20秒,這樣單位成本下降了,但是為了獲得一個好的答案其他成本都上去。

談焦慮:走出互聯網大廠的射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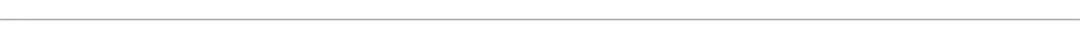
Q:今年感受到的行業實踐是怎樣的?B端和C端有什么不同?
王小川:今年大家更焦慮了,直接想走C端路線風險挺高的。在C端做事,如果沒有厚度,只是在做模型as service這件事情,在共識里面創業公司是沒戲的。一定得有產業厚度才行,要走出特色,做大家做不到的事,要比大家想得更遠,而且不只技術上的更遠,是在商業上、產業上想得更遠,如果還是在大廠的能力范圍內,這事沒什么好搞的。
我覺得大家太容易對技術仰望,但對技術產生的成果又是一種鄙視的狀態,覺得有所謂的“奴仆”給我服務,太分裂了。造助理不是錯誤,我們也做了百小應。但我認為,它不能代表大模型最前沿的東西。
Q:從移動互聯網時代到AI時代后,發現原來自己很多創業的邏輯是不適用的。你有什么心得?
王小川:可能是幾個變化:第一,核心的變化是產品的邏輯從PMF變成了TPF,PMF是產品和市場的fit,但是我們是供給側改革,市場需求已經在那了,現在需要考慮的是怎么能把它造出來,解決供給不足的問題,所以從PMF變成TPF;第二,是從琢磨用戶需求轉變成了琢磨技術是否能實現產品的各種能力,以及產品研發從造工具變成造“人”。
Q:大家今年和去年的焦慮也是有變化嗎?
王小川:去年焦慮買不到卡,今年焦慮有卡不知道該干嗎。
Q:賺不到錢,會算是焦慮的原因之一嗎?
王小川:我們繞過了大家競爭的主戰場,沒有這個焦慮。我的焦慮是讓大家怎么能把醫學問題和技術問題的信仰平衡好:別做技術的對醫療不關心,做醫療的也不追求技術。融錢、定方向、找人,是我們內部要不斷升級的地方,但是錢和方向上我認為是清楚的。
Q:依照你說的造醫生的愿景,未來都會參與到醫療的哪些環節?
王小川:短期肯定是先讓兒科醫生和全科醫生往基層走,使患者就診的路徑得以改變。再往下走,就能讓醫生有時間干更多事,這樣對科研也會有幫助。當他能夠實時跟患者打交道,能夠幫著更好地收集整理全鏈路數據,這樣就能有足夠的數據。最終,你的醫學模型是知道,什么樣的人該給什么樣的診斷和干預方法,在精準醫療里找到個性化的范式。
Q:從去年到現在,您被投資人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什么?
王小川:最早是怎么追上GPT-4是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,今年是大家都發應用了,你們怎么看?現在不這么問了,他們覺得做醫療挺好的。
Q:大廠和模型創業公司之間,接下來大模型創業公司會受到大廠的壓力?
王小川:肯定的,現在人才流動都開始往大廠流。走出大廠的射程,是這幾個(創業)公司都面臨的問題。所以大模型創業得走出共識,否則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。如果一個公司被看得特別明白,那就不是一個創業公司了。早年間,字節跳動也不被看好,好多大廠聊過都放掉了——非共識才是意義。走出大廠的射程,是我們當初下場的第一性原理。
長江DBA十二期班領軍企業家集結中,共同成就新商業文明思想者和引領者。

